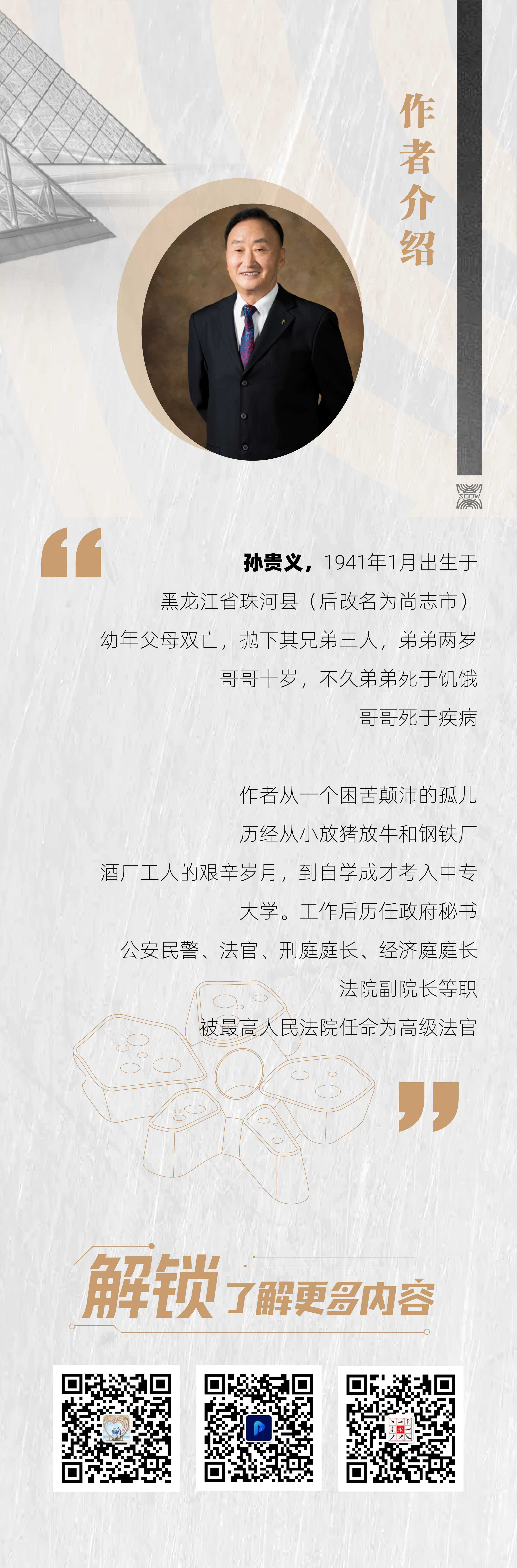岁月深处
往事已泛黄
却在回忆里闪烁光芒
苦难,是一条黑暗幽长的隧道。我曾在其中惊慌迷茫,痛苦挣扎,所以只能循着一丝微光寻找尽头的出口;
苦难,是一道利剑闪烁的寒光。我曾在它面前伤痕累累,心生畏惧,所以只能迎着利刃磨砺一身坚强的盔甲;
苦难,也是一份裹挟着寒冷与温暖、邪恶与美好、痛苦与欢乐的礼物——让我的生命如此丰盛!
在苦难中走过,如今打开那个沉重的包袱,发现它不是命运对个人偶然的重击,而是一个时代之于当下社会的映射;
苦难,也不是时间对个人严酷的考验,而是一段历史赋予整个民族的悲痛!所以,我经历的苦难,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滴水,是岁月沧桑中的一粒沙,倒映出时代的画面,见证着社会的变迁!

在每个人的人生历程中,童年都是最难忘的,而我的童年却是因为悲惨而刻骨铭心!那些痛苦的经历,犹如一道石头上的印痕,镌刻在我的心上,无法抹去,难以忘却!
我是一个孤儿,关于家族的历史和苦难历程,是成年后抚养我的姨娘张桂兰讲述给我的——
我父亲叫孙熙盛,于1909年出生在山东省昌邑县(传说是一个叫柳潭的村镇)。父亲在老家时,读过私塾,从他给我们哥仨起的名字和他所从事的职业看,他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。父亲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二,大伯的名字不详,叔叔叫孙熙仁。
父亲与叔叔于上个世纪初同家族亲系孙贵德全家(孙永祥之父,孙美娟爷爷),从山东省昌邑县“闯关东”来到当时的珠河县(建国后依据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名字改为尚志县),据说同来的还有贾树桐的父母,孙连生等人。
说起“闯关东”,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,在当时,“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”东三省因地处山海关以东,故被称为“关东”。
自清朝初期至新中国成立,由于自然灾害、战乱等原因,迫于生计的华北穷苦百姓或从山海关,或从渤海湾分陆海两路闯荡到地域辽阔、资源丰富的关东大地谋求生存。而这浩浩荡荡的“闯关东”人潮中,以山东人最为居多,父亲一家就随着这场迁移大潮,从山东老家来到了黑龙江。
从山东到黑龙江,这条在今天看来并不算遥远的路程,对于当年“闯关东”的人们来说,却是一条异常艰辛的“生死征程”!不知有多少人在路上被饿死、累死或是病死。
父亲他们是经历了怎样的艰苦跋涉,忍受了多少疲惫、病痛和饥寒,才踏上了关东大地我已不得而知。只是听姨娘说,父亲来到珠河县在一面坡一个叫同鼎南的酱园子跑外柜(即购销员),叔叔也在酱园子当工人。

民国23年(即1934年),17岁的母亲与25岁的父亲结婚,住在当时的珠河县富贵桥西,也就是建国后的尚志印刷厂后院的一个草房,是一个单独的小院。我记得离院门外不远还有一口水井,姨娘说我小时候淘气,倔脾气上来还曾经跑去想要跳井,被我母亲“抓”回来打了一顿!
我外祖父家就住在当时的珠河县城关镇(后来的尚志镇),家中有外祖母和我姨娘,我母亲家里姐妹俩,母亲是老大,还有一个从我四外祖父过继过来的舅舅,名叫张会堂。我外祖父在家中排行老五,外祖父当时在距他家三四百米处的黄土岗开了一个泥缸窑,雇了不少工人。因我外祖父在关里老家是个有名的制缸技术窑工,能烧制出各种形状大小不一的泥缸,舅舅负责监管烧缸的销售。
父亲与母亲结婚后不久,于1935年生育了我大哥孙贵仁,1940年腊月二十生育了我,1943年我弟弟孙贵礼出生。当时靠着父亲在酱园子跑外柜挣的钱,我们一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。

父亲总是穿着一件深色暗花的绸缎大褂,一双黑皮鞋,戴着个圆项“商人帽”,这样一身装扮,把身材高大的父亲显得格外“精神”。平日里,他就是这样一身“职业装扮”出去跑外柜,那时年幼的我,总是跟在父亲身后,让他带我一起去酱园子。父亲也很宠我,时常就把我带到酱园子玩。
有一次我又跟着父亲在酱园子玩了一天,晚上回来时,天下起了雪,风又很大,父亲背着我没有赶上回珠河的客车,只能搭乘货车回来。
那时候东北的冬天,寒风像刀子一样,在敞篷的货车上,父亲突然松开了搂着我的双臂,我正要喊冷,他却将自己的围巾摘下来,围在我的脖子上。
瞬间,一种软软的、暖暖的感觉包围了我小小的身体!而那个凛冽寒风中,父亲为我围围巾的画面,也定格在我心中,让我记得自己也曾经被父爱怜惜与保护!

母亲在家照顾我们三个孩子,得空时还会摊些煎饼。许是因为山东人都爱吃煎饼,母亲摊出来的煎饼又薄又软,回味香甜。我们自己吃不完还会分给亲属邻里,大家总是赞不绝口!
家中小院仓房内的那个小石磨,在磨面粉时发出的“吱吱”声,成了萦绕在我记忆之中,最最温暖动听的声音!
然而,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随着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,在战争阴霾的笼罩下,百姓的生活随时都会飘起“不测风云”,一个家庭简单快乐的“小日子”终归要被一个民族血雨腥风的“大灾难”夺走!

1945年1月,随着太平洋战争进入尾声,面临战败的日本鬼子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垂死挣扎,为与苏联红军“决一死战”,在密山虎头要塞修筑大型的战争工事,在东北各市县到处抓劳工。无数个家庭被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之中!
伪县府给父亲工作的酱园子摊派了两个劳工“指标”,由酱园子指派,酱园子总共就十几名工人,当然谁都不愿意去。大家都知道,给日本鬼子当劳工修筑军事工事,除了病死就是被日本鬼子处死,基本上是“有去无回”。

酱园子只好采取抓阄的办法来决定劳工人选,命运使然,父亲抓到了“去”,而且当时的珠河县公署只给了十天准备时间,为防止出工的人逃跑,采取家庭联保的办法,由我家和在珠河县城关镇开缸窑的外祖父家联保。
面对即将去给日本人当“劳工”这个事实,特别是父亲接到了珠河伪县署正式通知后,我们家被阴云笼罩,沉浸在无奈的痛苦中。父亲和母亲抱头痛哭,我们三个孩子虽然不知发生了什么,也跟着一起哭。
之后,父母领着我们三个孩子去了姥姥家,姥爷姥姥和姨娘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,又是一阵大哭。
伪县长沙子图算是姥爷家的“西邻”,父亲原打算让姥爷托人找他说说情,姥爷摇着头唉声叹气地说:“虽然与他家住了四五年的邻居,但平时没有任何联系,平日见他坐着轿车出出进进,大院戒备森严,根本说不上话!”
父亲听后,在众亲面前,拿出那张“索命通知单”低下头沉思良久,然后抬起头,泪眼望着我们,往日里那和和美美的家庭氛围一去无返了,而可怜的父亲——也是我们一家人唯一的生活支柱,即刻就要倾倒,步入那无底的深渊,而这一切不幸的根源就是万恶的日本侵略者!
从姥爷家回来,我们哥仨早早地睡去,次日清晨起来,看到父亲尚未睡醒,母亲拖着疲惫的身躯正在做饭,我哥凑到灶台帮着母亲烧火,我娘对他说:“你爹昨晚折腾了半宿,病了有点发烧,我给他拔了火罐,稍微好些刚刚睡下,吃完饭我和你爹到诊所去看看。”
饭做好了,我娘怕影响爹爹睡觉,悄悄地把还在睡觉的弟弟抱出来叫醒,我们一起在外屋地吃完了早饭。不一会父亲醒了,满脸通红,像有火苗罩着的样子,还伴着咳嗽,无精打彩地坐在炕沿上,沉闷无语,我娘上前问他:“感觉咋样?”
他回答说有点发烧发冷,已经一天一夜没怎么吃东西的父亲,已见削瘦。父亲的结拜至交以及珠河县城知名的显贵商人,得知我爹摊上劳工了,都来看他。他们都说,前些年抓劳工,都是从农村拉青壮劳力出劳工,可能是农村抓的差不多了,今年是头一次在城镇抓劳工,这真是倒霉啊!
大家只能抱着同情之心,劝父亲放宽心,并表示他们会帮忙照顾家里。他们走后,我娘劝爹吃了几口饭之后,同时又去找了个老中医来给爹诊脉,说是起的羊毛疔,给父亲扎了针,老中医临走告诉我娘,让病人多喝开水,不能吃生冷,不要着凉。
这样坚持到第三天下午,父亲病情愈加严重了,舅舅用牛车将父亲拉到双桥子镇内仅有的私人小医院,医生诊断认为病情严重,需要住院治疗,我娘和叔叔留在医院伺候我爹,我姥爷和姨娘回到我家,姨娘留下看护我们,姥爷他们就回家了。

父亲住院的那天,也是腊月二十三,往年这个时候全家都喜气洋洋地忙着过年了,而这一年,起先全家都没有心思张罗过年的事。但是爹住院后,娘便给了我姨一些钱,让她去买些年货,操办过年的事,她对姥爷说:“也许过年的喜气能冲走孩爹身上的病魔,如果不能,也要在他走之前,和他一起再过一个祥和年!”
就这样,姨娘置办齐了年货,我娘抽空回来,炸了一些我们爱吃的干果和肉面丸子,并与我姨包了些饺子在小北屋冻上了,我姨事先打好酱糊,我娘同哥哥他们三人在门上贴上了对联,屋里墙上还贴了充满喜庆的年画!
家里有了浓浓的年味,娘煮了饺子给我们吃完,又带了饺子和炸的面食给我爹送到医院,平日里饭量很大的父亲,却只吃了二三个饺子便不想再吃了,接着又是一阵头痛迷糊,高烧不止,浑身直打冷颤!
就在这时,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,是我姨领着一面坡同鼎南酱园子的老板和老板娘,还有六七个伙计来看望父亲了。他们是特地坐火车过来的,安慰父亲好好治病,盼他尽快康复,临走,酱园老板还给母亲留下一些钱。
后来,父亲在医院治了几天也不见效,家人考虑再有两天就是除夕了,所以决定把爹接回家过年。父亲从医院回到家,见到门上贴的对联、福字,过年的喜庆氛围让他的心头有了片刻舒展。然而,努力燃烧的一点点微光,无法照亮阴霾的天际,父亲还是在三天后离开了我们!
那是五岁的我,第一次面对死亡!父亲静静地躺在那里,昔日高大魁梧的身躯已仅剩一副干瘪的骨架。母亲俯在他身边,痛哭不止,哥哥一手抱着弟弟,一手拽着我,跪在父亲床边哭泣。紧张和恐惧充满了我的心,脑海中又想起那个寒冷冬日,父亲在货车上给我围围巾的画面……

1944年腊月,父亲走后,家里的顶梁柱倒了,母亲哭了两天之后,只能收起悲伤和柔弱,坚强的撑起我们的家!她就靠摊煎饼、接手工活养家,外祖父也时常给些零钱贴补家用。
当时,叔叔托人向外祖父提出“嫁嫂养子”的要求,这是那个贫瘠的年代,一种特殊的“习俗”——丈夫去世后,妻子可嫁给丈夫的弟弟。一方面可以解决兄弟多的家里,弟弟无钱娶媳妇的困难,一方面可以让失去丈夫的妻子继续依靠“男人”维持家中的生活。但是母亲拒不同意,因为母亲非常了解他的为人,不务正业,挣几个钱还不够他自己祸害的。母亲拒绝了他的要求,这也给日后叔叔不愿抚养我们埋下了“祸根”!
父亲去世的第二年,母亲也患上了重病,下不来坑了,医生也束手无策。叔叔不得不和姨娘一起来家里照顾我们几个年幼的孩子。不久,在我五岁那年(1945年)的腊月,母亲也病重不治去世。叔叔与舅舅张会堂,把我们三个孤苦伶仃的孩子送到我外祖父家后,就回到了一面坡,当年我哥哥孙贵仁十岁,我弟弟孙贵礼刚两岁。

外祖父家是一个有六间茅草屋的院子,位置就在现今尚志镇“知识分子家属楼”后面的北胡同道路东侧。而当年那条路的西侧,就是伪县长沙子图的“沙家大院”,那是一个四面砌着高高的院墙,四个角楼都有警察把守,警戒森严。外祖父家的院子与它东西相望,院子里的六间茅草屋 ,东面三间由我外祖父和外祖母及我姨娘居住,东屋三间房夏季时是我外祖父开缸窑雇的窑工住的,冬天就闲置着。
我们哥仨开始就和我外祖母住一起,后因外祖母一到冬天就犯严重的气管炎,咳嗽不止,屋里烧个火炉子,炕上还有个火盆取暖,弟弟因为太小不懂事,总用手去扒火盆,外祖母有病无力看着他,就让我哥哥和我看着他。
后来外祖父看弟弟有时因吃不饱哭闹,姨娘每天还要给家里做饭,与舅舅到市场买的炉筒子在东屋盘了一个火炉子,我姨就领着我们哥仨搬到东屋住了。白天就由我们哥俩看着弟弟,有时我姨也帮着照顾,她每天给弟弟单独熬点玉米面糊糊,我和哥哥就同家里大人一起吃。
转眼几个月过去了,外祖母的病越来越重,有一天我姨突然从外祖父那屋回来大哭一场,我同哥哥问她,她还是一直哭,后来姨娘告诉我们,外祖母病重昏过去好几次了,“我白天不能来照顾你们,晚上也不能来陪你们睡觉了”,姨娘哭着说让哥哥哄着弟弟睡觉。
没过几天,我叔叔突然从一面坡来了,我先是听到外祖父屋里传来几个大人和叔叔吵架的声音。后来,叔叔过来说,他被舅舅好一顿骂,因为他把我们哥仨放到外祖父家就不管了,外祖母病重没时间没能力照顾我们,他要把我们接走,哥哥问叔叔:“啥时跟你走?”叔叔说得等等,他也没有房子,住在酱园大炕,得回一面坡与酱园子掌柜商量后再说。
叔叔当天就走了,他走后姨娘跟我们说,叔叔答应尽快就把我们接走。但哥哥对姨娘说:“母亲活着的时候叔叔对我们就不好,我们不想和他一起生活。”哥哥还说,弟弟太小,叔叔成天上班没时间管,但姨娘哭着说,现在家里就这个情况,你姥姥好几天不吃饭了,炕拉炕尿,也就是这几天的事,我和哥哥也跟着姨娘一起哭了起来……
后来没几天外祖母就走了,在院子里搭了大棚设了灵堂,外祖父的亲朋好友不少都来吊丧,人来人往,就在停丧的第二天,我叔叔闻信也来吊丧了。
翌日早上,外祖母出殡,被送到珠河县高贵桥东纪国士寺的墓地下葬(这里在建国后被改建成火葬场)。
出殡回来,家里人才开始吃午饭,我们小孩不让上桌,姨娘拿了一点饭菜让我们回到屋里吃。不一会儿,姨娘吃完了饭,又给我们端了些饭菜过来,告诉我们叔叔这次来,就是要把我们带走的,听到这个消息,我们哥仨伤心地哭了起来,不愿意跟着叔叔走。
姨娘说:“你姥爷说了,先让你叔带你们走,实在不行再回来。”我哥就问:“把我们领去有房子吗?我们住哪里啊?”姨娘告诉我们,叔叔现在没房子,暂时在酱园子住,得找到房子后再搬出来。

就在当天下午,那个寒冷的早春时节,房檐的冰排还在滴水,姨娘给我们哥仨收拾了“铺盖卷”,打成一个大包,装上了姥姥家的牛车,姨娘和我们一起上了牛车,她告诉我们她和我们一起去一面坡。叔叔也跟着上了车,姥爷也拄着拐棍出来送我们,并嘱咐哥哥要照顾我和弟弟,舅舅张会堂赶车将我们送到珠河县火车站。
姨娘跟我们一起上了火车,大约不到一小时就到了一面坡火车站,叔叔拎着大行李包,姨娘抱着弟弟,哥哥领着我一起奔向叔叔工作的酱园子。
这个酱园子在一面坡最出名最热闹的南市场旁边,一个小门市房的后面,是一个很大院落,门市房旁边是老板家住的大三间砖瓦房,院子的西南盖的很宽敞的土坯房,是酱园子的生产车间和原材料产品仓库,东侧一排房子是工人房,屋内有两三个间隔好的套间是大领班住的,剩下东西二排火炕就是我们住的,十几个大小铺面中间没有间隔。那房子北间间隔有个厨房和吃饭的小食堂。
老板和老板娘看我们来了倒是很热情,先是领着我们把行李放在炕头,然后就领着我们一起到食堂看了一下,厨房和食堂是连在一起的,有两三个桌椅,厨房有两个人在做饭,老板介绍说:“工人过了年刚上班,工人快下班了,一会做好了你们先吃。”
叔叔说:“孩子他姨还要回珠河。”老板就催厨子快点做,厨子很快就把饭菜做好了并端到桌上让我们吃,菜是白菜炖豆腐里面还有点肉,还有两小盘自制的小酱菜,主食是玉米豆面大饼子。折腾一天,我们早已饿了,吃的特别香特别快,姨娘看我们吃饱了,也安顿好了,心里很高兴,就跟我们说:“你们一定要听叔叔的话,有空我再来看你们。”说完叔叔就送她去了车站(姨娘那年才14岁,仅比我大9岁)。

就这样,在我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春天,即1946年春,我们哥仨安顿了下来。在那之后,叔叔每天照常上班,我和哥哥哄小弟玩耍,按时到食堂吃饭。天气渐暖,我和哥哥就领着小弟到酱园子不远的南市场溜达,看看热闹。
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,老板和酱园子的工人就对我们产生了不满情绪,原因出在弟弟身上,他白天由哥哥哄着不怎么哭闹,可是到了晚上就总是哭闹不止,找爹找妈,毕竟他才刚刚两岁!我们越是哄他哭闹的声音越大,不仅影响叔叔休息,也影响其他工人休息。
那段时间叔叔算了一笔账,他一人挣的钱供我们一家四口花已很紧张,再加上弟弟哭闹影响别人休息,酱园老板就催我叔叔赶紧搬出去,花销上就更加吃紧了。叔叔在酱园附近找了几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,后来酱园的一个工友说在车站天桥附近有个房子,叔叔就找到了那里。
房主是个五十多岁的河南老太太,人看上去挺和蔼的,之前有个租客已经搬走了,房子一直空着,叔叔一打听,房费还不高,每月也就块八角的。
叔叔租下了这个房子,我们随即开始搬家。叔叔找了个小驴车驼着我们的行李和棉衣,还有老板娘在食堂拿的几个盆和碗,以及一些酱菜,他还在市场买了些苞米面和豆面。

我们搬到了新租的房子,房主奶奶把我们四人领进屋后,问叔叔是不是孩子的父亲,叔叔告知是我们的叔叔,不是父亲。她进而疑惑地问叔叔:“孩子妈妈呢?”叔叔说:“去年都死了,就剩这三个孩子了!”
老太太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们忍不住说了一句:“太可怜了!这么小今后可怎么生活啊?”说着,她用帚扫把火炕席子扫了一下,接着又给了我们一口洗净的铁锅,当得知我们还没有吃饭,她主动和面用铁锅贴了饼子给我们吃,接着又问叔叔:“这几个孩子每天吃饭怎么办呢?”叔叔说:“我每天上班哪有时间给他们做饭,让老大学着做饭呗!我每天要早起做酱,所以不能在家住!”
老太太一听马上说:“你不在家可不行,这三个孩子这么小怎么能顶起这个房子?再说最小的这个才三岁没有人照顾怎么行?小哥俩也哄不了小孩啊!晚间起夜都不敢出屋吧?你给他们准备一个洋油灯和尿盆吧。”说的叔叔无言以对,只好答应说他考虑考虑。
接着老太太又说,孩子们做饭还没有柴火,今天是用她的柴火做的饭,要不上南山砍些柴或上市场买。说着饭就好了,我们吃饭时,老太太便回去了。我们搬到新房的第一顿饭,是两合面饼子就酱园的酱菜和凉开水。
吃完饭,叔叔还是坚持要到酱园去住,说他早上要上早班,我和哥哥都哭着求叔叔:“贵礼太小了,晚间我们俩哄不了,再说我们半夜上茅房也不敢出屋啊!”弟弟看我们俩哭他也跟着哭,叔叔看到这种情形,只好答应不走了。但是他的铺盖没搬过来,便又回酱园去取,回来时还买了尿盆和一盏洋油灯、一瓶洋油。他回来不多时我们哥仨就躺下睡着了。那天晚上,弟弟没哭没闹,我们都睡了一个好觉。
因为叔叔起早去上班,所以很早便把哥哥叫起来,教他贴大饼子,叔叔走后,哥哥又睡了一会,我们起床后吃了早饭,依然是大饼子就酱菜。从那之后,多数时候都是哥哥做饭,而且基本上是上顿大饼子咸菜,下顿咸菜大饼子,而且是生一顿糊一顿,有时没有开水,我们就喝凉水。
叔叔很少回来了,有时咸菜也没有了,只能就着咸盐粒子吃大饼子。弟弟小不懂事,有时大把大把地吃咸盐,现如今人们为了健康倡导“低盐饮食”,从科学角度讲一个成年人每天吃盐的量不应超过6克,但那时刚刚三岁的弟弟,却被饥饿所迫,咸盐成了他唯一可以充饥的“主食”。
这种盐也不是今天细白的“精盐”,而是粗加工的“粒盐”,发黄的咸盐粒经常从弟弟枯瘦的小手里散落,弟弟就再去抓,直到把它们塞进嘴里,然后撇起小嘴哭着咽下去,和今天吃着巧克力喝着各种饮料的小孩子,简直是天壤之别!
没多久,弟弟的气管就被咸盐“齁”出了病,咳嗽不止,我们连饭都吃不饱,哪有钱给他买药呢!本就营养不良、体质很差的弟弟,在来到这个世界仅仅三年后,便活活被盐“齁”死了。
在他那么短的生命里,没有幸福只有痛苦,没有欢笑只有泪水,甚至连父母怀抱的温度他都未曾好好感受,甚至没有来得及叫一声哥哥,便匆匆离去了!或许,是这世界太苦了吧,那么小的弟弟真的不想再煎熬下去了!

按照当时的丧葬风俗,小孩夭折是不给用棺材的,男孩用谷草拧成绳拦腰绑三道绕,女孩绑二道绕,叔叔没有找到谷草,便用一个火柴箱子将弟弟的尸体装里抬到南大庙旁的墓地扔了。
寂静的山林,寒冷空旷,我和哥哥忍不住回头望去,许是弟弟太小太轻了,那个装着他的火柴厢子几乎快要被风掀起来,可是弟弟再不会哭闹了,也再不会感觉到痛苦了!他静静地躺在那里,人间的滋味对他来说,或许只是苦和咸!
如今,我还时常想起弟弟,他冻得通红的小脸,哭得肿肿的眼睛,都在我脑海依稀可见!